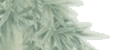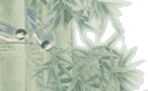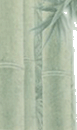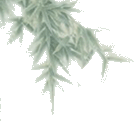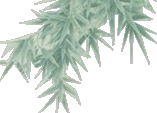|
以水取勝的“北國江南”大觀園中的廣闊水面,使很多紅學家疑惑不解,書中明確交待,大觀園是寧榮二府的後花園,寧榮街熱鬧非凡,必定在市中,那麼園中水源從何而來?引起讀者不解的,“引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寶玉指出: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這段作者的“追蹤躡跡”的描述,使大觀園的廣闊水面有了“源泉”----外河。
根據研究可知大觀園在理水方面十分講究,一是園中水面廣闊,“銜山抱水”的大觀園中,有池塘、清溪、內河、引泉,“處處不離水”,有堤,有岸,有港灣,這樣的“以水取勝”的私家園林,實在難尋。二是活水潺潺,有“外河”水源,有進水之閘,完全可以滿足園中各處水景的需要。三是依水建築多,水面活動多,這是典型的江南建築風格,北方少見。藕香榭、滴翠亭、蘆雪庵、凹晶館、紫菱洲……。
故事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登過採蓮船,菊花詩會、凹晶館聯詩、蘆雪庵即景詩等都在池邊吟成。要尋大觀園的原型,必須要有足夠水面的私家園林,而僅這點在北京城內就很困難。
據史料記載,康熙年間曾頒佈“非御賜,不準引用什剎海水”的禁則。禁令一下,內城的府邸花園斷絕了水源。雍正年間和乾隆初期,禁令照行,一直到乾隆中晚年,才有所松動。所以在曹雪芹寫書的年代,即便是王府花園,水面也是很受限制,絕不會從“外河”引進晶簾一般奔入的活水。
在南京城的隨園,水面也很有限,根本無法與大觀園相比較。
“廣可百畝強”的水西莊,卻恰恰能滿足這些條件。水西莊一直以水面取勝,譽滿江南江北,詩人學者來此,無不對此感慨萬分,留下的詩篇,很多寫下了水西莊池塘、溪流的景
象。水西莊“二分修竹三分水”,表明它園內水面的面積很為廣闊,可以乘舟遊賞,園中池塘名叫琵琶池,依水建築很多:藕香榭、枕溪廊、數帆台、苔花館、泊月舫……。
與大觀園水源相同的是,我們很容易找到水西莊的水源----衛河。水西莊即在衛河之畔,從“外河”利用橋閘,引來晶簾般運河水。三面環抱的衛河可以源源不斷地供給水西莊水面的水。
花紅蕉綠“花神廟”《紅樓夢》第27回,提到大觀園眾少女餞花神的風俗。第78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誄,寶玉懷念屈死的晴雯,小丫頭哄他:晴雯是上天司花,專管芙蓉花的花神。寶玉信以為真:“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個神,一樣花有一位神之外,還有總花神。”大觀園中前後兩次提到的“花神”,在紅學研究中一直也是一個課題,因為在清朝供奉“花神”的廟宇罕見,芒種祭餞“花神”的習俗也少見。史書記載,清朝康雍乾時期,天津衛河邵公莊、小西關一帶,種花養花賣花的人家很多,邵公莊的海棠遠近聞名以至又名“海棠莊”,豔雪樓即是以“消魂海棠”而命名的。春日來臨,水西莊周圍幾乎是花的海洋,花匠們信奉“花神”,自發地在運河邊建起花神廟,且香火旺盛(《天津史誌》1993
年第3期,作者顧道馨)。《津門詩鈔》載,天津詩人殷希文寫有《花神小祠》一詩:“數椽如斗附垣低,俎豆花神小有祠。最愛留題佳句在,碧雲紅雨耐人思。”《紅樓夢》中第43回,賈寶玉為祭金釧,來到水仙庵,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卻只管賞鑑。”對水仙洛神不信不拜,而對花神、芙蓉神卻完全相信。這是否也說明在作者寫書的環境中,真正存在著祭祠花神的“花神廟”呢?時至今日,天津南運河水西莊遺址旁,仍有花神廟的地名,老人們可以回憶出花神廟的興盛場景。
元妃省親與孝賢皇后巡幸水西莊,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第一回,即特地言明,書中幾個悲歡離合的女子是作者“親睹親聞”,記述時“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
曹雪芹在清朝乾隆年間寫書時,有巨大的壓力,書中必須“毫不干涉時世”、“故將真事 隱去”才能將《紅樓夢》流傳於世。但是作者又極其渴求後人“誰解其中味?”使讀者能夠理解他的隱衷,揭開隱去的“真事”面貌。書中有兩個情節,寫得既真實入扣,又“不合情理”,這就是“元妃省親”與“秦可卿喪事”。元妃省親不要說清代絕無此例,就是考查歷代皇妃也沒有如此“省親”的。秦可卿喪事則更超出一般規格,基本上是一位皇后級的國喪標準。
元妃省親在清代和歷代都沒有實例,元妃省親的藝術原型是乾隆孝賢皇后,她於乾隆十三年冬末,隨皇帝東巡時,巡幸運河邊的水西莊。第18回“元妃省親”這一情節,寫得真實具體,絲絲入扣,細節分明,仿佛引導讀者親臨其境。在這幾段文字中,脂批很多,在豪華肅穆的皇家禮數中,脂批:“形容畢肖”,“難得他寫得出,是經過之人也”,“《石頭記》最難之處,是別書中摸不著”,“真有其事”。
在封建集權社會裡,“別書摸不著”的,只有皇帝、皇后行動的實錄。此段有一重要脂批:“《石頭記》慣用特犯不犯之筆,真讓人驚心駭目讀之。”曹雪芹敢於將皇室活動“畢肖”寫下來,這種觸犯最高統治者的寫法令人擔心,這是“特犯”。而脂批中“不犯”之筆,又在替作者開脫,這是作者親身目睹之事,並沒有誇張虛構的罪名,真實再現並無錯誤。表明“元妃省親”描寫全部有事實根據。在戚序本第18回後有一大段重要脂批:“此回鋪排,非身經歷,開巨眼,伸大筆,則必有所滯墨牽強,豈能如此觸處成趣,立後文之根,足本文之情者?且借象說法,學我佛闡經,代天女散花,以成此奇文妙趣。”
“元妃省親”這一情節的生活素材,也不會是帝后外出遊幸皇家苑囿,而是帝后外出巡幸某處私家園林。因為整個準備活動是賈府為迎女兒元春省親而進行,“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幔,指出賈府人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啟事,儀注不一。……”
這段描寫多麼細緻入微,顯然是以某處私家園林為事實根據的。如果帝、后在自已宮內御 花園或宮外皇家苑囿遊幸,沒必要有那些禮節,也不用那麼繁瑣。很多紅學家和讀者,在“元妃省親”的文字中,感到了“賈元妃”的後面隱藏著一位“真皇后”。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元妃省親中的皇家儀仗,儀仗規模超過貴妃待遇,更重要的是,公然出現了“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夔頭”,這龍鳳裝飾是帝后的專用儀仗用品,其它給別的嬪妃是絕不能隨便使用的。這一細節不知是作者有意露了破綻,還是無意中將現實中親眼見的帝后儀仗寫入書中。反正“賈元妃”的儀仗反映了她的真實身份是一位“真皇后”。這正是作者大手筆高明之處,用一處細節描述達到“泄露天機”的目的,既做到了“真事隱”,又能使後人“解其中味”。
脂批最重要最直接點明“元妃”身份的是一條大膽的批:“文忠公之嬤”。這是在第16回,賈璉、鳳姐談議元妃將要省親,趙嬤嬤說:“這樣說,咱們家也要接大小姐了?”庚辰本在這段旁側朱批:“文忠公之嬤。”“文忠公”是乾隆時大學士、一等公傅恆,乾隆皇后的弟弟,顯赫一時,於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去世,死後謚“文忠公”。其家大小姐自然是傅恆之姐----乾隆帝的孝賢純皇后。只有非常熟悉傅恆家人動輒提到“咱們大小姐”這種口吻才能寫下這批語。
另外,《隨園詩話》舒敦批語中提到:“乾隆五十六、七年,見有抄本《紅樓夢》一書,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恆家。”這兩種說法如此相同,就不是單文孤證了。實際上也只有孝賢皇后才有資格和可能省親,從“文忠公之嬤”這批語和“傅恆家事”來分析,真正能省親的“元妃”的生活原型,應是孝賢純皇后。
還有許多讀者,不明白“元妃省親”為何時間一定要選在冬末?從史料得知,乾隆十三年二月初,帝、后乘船順運河東巡,途中路過南運河畔水西莊,按原定計劃,帝、后巡幸了這座著名大型園林,水西莊舉行了盛大迎帝后儀式。整個活動恰好在冬末。乾隆皇帝帶著孝賢皇后東巡,過天津後,到德州,下船去泰山、曲阜,回京途中卻發生意外,孝賢皇后在運河落水而亡,時間是三月十一日。皇后死因,眾人皆有“疑心”,野史中有大量記載,主要說法是乾隆與皇后的弟媳通奸,被皇后撞見,乾隆酒中惱羞成怒,最後結果是皇后落水而亡,乾隆帝酒醒後甚為後悔,輟朝九日。皇后的遺體由御船運回,到北京通縣,群臣隆重舉行儀式盛大的葬禮。這件全國震驚的皇后暴死案,曹雪芹當然會注意到,皇后巡幸水西莊與皇后暴死,也會引起他的強烈興趣,“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正是這位皇后的真實寫照。
乾隆十二年,水西莊進行了大規模擴建,使原來“百畝名園”又增加了新景點,五月擴建完工,十一日查為仁率子及女、媳妾等舉行了盛大的賀新園落成詩會。這一次建園詩會,女詩人們大展奇才,在津門轟動一時。“元妃省親”時也在園中請幾位女詩人,賦詩歌頌。其中薛寶釵:“芳園築向帝城西”,其韻與水西詩會相同。而迎春“奉命羞題額曠怡”和李紈“奉命多慚學淺微”的口氣,與水西詩會也是一致的,且都是女詩人歌詠園林。
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九日,為迎乾隆東巡,遷查禮妻李欽墓葬。據《銅鼓書堂遺稿》卷三十一《亡妻李安人遷厝小誌》載:“天子將幸東魯,天津為鳳艒必經之地,於是津之人謂翠華臨幸,不可無駐蹕處,相度地勢,惟水西莊為宜,而吾妻權厝猶在莊北,爰有遷厝之舉。”據《天津縣新誌》卷首“巡幸”記載:“乾隆十三年二月高宗東巡,三月回蹕。臨幸天津,恩恤長蘆鹽商,詔免次年錢糧十分之三,賞賚軍民七十八以上者。”在水西莊受到盛大歡迎,是否能借機見到親人,史料未詳記,但孝賢之弟傅清一直任天津鎮總兵,在津有住宅及親屬,近年尚發現明義----傅清之子的一束信扎,發現地點就在天津。僅僅一個月,冬去春回,孝賢皇后卻在運河上不明不白地死去。正如《紅樓夢》中所言:“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拋。蕩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
孝賢皇后死前怎麼痛苦,這已是一個無法解開之謎,但她“死不瞑目”是肯定的,“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呀,須要退步抽身早!”這裡的訣別囑托,應有所指,她的親弟弟傅清官運亨通,卻於乾隆十五年,即孝賢皇后暴死之後二年,自殺身死。另一個弟弟傅恆,也因夫人之事家宅不寧。這些舉國上下沸沸揚揚傳播之事,使曹雪芹可以用藝術手法寫成元妃形象,而她的盛衰悲劇,使賈府的興衰有了根據。可能因為皇后暴死,死前巡幸水西莊這一盛舉,史料上記載得比較簡單,查氏準備了一年時間迎駕;而巡幸過程卻只有幾個時辰。乾隆初期,文字獄尚嚴厲,涉及帝后的行蹤,不敢留下細節描述。只言“帝后臨幸天津,途中預備彩棚戲台,並設有採蓮船隻等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