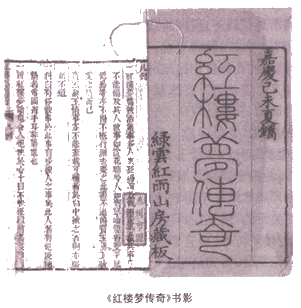|
《红楼梦传奇》成稿于嘉庆三年(1798年)。在这以前,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秋,即《红楼梦》程甲本出版的第二年(发行的当年)已写成《葬花》一折(见《红楼梦传奇》作者自序),早于孔昭虔嘉庆丙寅年(1796年)编写的《葬花》四年。所以仲氏乃改编《红楼梦》为戏曲的第一人。仲氏《红楼梦传奇》写成后,嘉庆四年由友人刊于京师。此后,已知的尚有同治年间友于堂刻本,光绪三年(1877年)上海印书屋排印本。
《红楼梦传奇》共五十六折。前三十二折写《红楼梦》本事,而后二十四折则是写的《后红楼梦》故事,与曹雪芹、高鄂的《红楼梦》无关。所以阿英在编《红楼梦传奇》时,只选用了前三十二折,这是很有见地的。仲著《红楼梦传奇》前三十二折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基本忠于原作。他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是将长篇小说《红楼梦》改编为全体戏曲的第一人。在没有多少前人经验可作借鉴的情况下,将《红楼梦》这一巨著改编为全本戏曲,确非易事。正如他在剧本凡例中所说:“红楼梦篇幅浩繁,事多人众,登台演戏,既不能悉载其事,亦不能遍及其人……不过传宝玉、黛玉、晴雯之情而已,有移此事出有因于彼事,有移彼人之事于此人者……”他删繁就简,突出主线,集中概括,浓淡相宜,这说明仲氏是深得改编戏曲的三昧的。这在今日也许只是常识性的问题,但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见识,并不是很容易的。仲氏的这一尝试,不能不说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葬花》一折中,他将葬花与共读西厢移并于一折之中,使情节较为集中。今人改编的《红楼梦》戏曲,也将这两节并在一起,如果不是受他的影响,也是所见略同。
二、《红楼梦传奇》把贾母作为鞭挞的主要对象。在他的笔下,与高鄂续书一样,史太君是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这是很有见地的。为了突出贾母的凶恶形象,他把贾母用净角扮演,实在是很大胆的。在《焚稿》一折中,在黛玉垂危时,贾母前去探望,说什么“孩子家从小儿一处顽笑亲热是有的,到了懂人事就该分别些,才是女孩儿的本分,我才疼他,若是他有别的念头,成什么人了。(冷笑介)我可白疼了他呢。从来医心无药,林丫头果若是心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贾母的阴险冷淡,跃然纸上仪征詹肇堂在剧本的题辞中写道:“填词若准春秋笔,首恶当诛史太君。”显然是受了仲氏在改编剧本时,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的根源有着深刻理解的,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曾是封建官吏的仲氏本人,能用戏曲的形式来揭露和鞭挞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残酷,更是难能可贵的。
三、仲振奎不愧是个戏曲家,他通晓音律,熟谙曲牌,填词才能极为杰出。《红楼梦传奇》的韵文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其特点之一是富有抒情性,缠绵悱恻,哀婉动人。如在《鹃啼》一折中,李纨哭黛玉时唱:“才非福,艳难留,玉人偏厄运;叹泡沤,万种悲凉态,离魂时候,竹梢残月挂帘钩,灯光暗如豆。”情景交融,令人听后萦回脑际,久不能忘。其特点之二是形象鲜明,借物寓意,比喻恰当。如《焚帕》一折中黛玉在焚帕前唱:“俺只为苦仁儿个中如杏,俺只为怕飘风波面如萍,俺只为靠周亲免叹机丝命,俺只为爱彼温柔心性。谁知道没相干云消天净,还说什么春花结冢,秋雨挑灯,鲛绡寄泪,诗句含情。值不得回头一笑却冰冷!”这一连串形象化的比喻,道出了玉人心境,哀婉凄凉,催人泪下。
此外,出语浅显,雅俗共赏。如在《索优》一折中,宝玉被打后黛玉的一段唱:“如雨泪滂洋,透了罗衫又罗裳,更谁人仁爱似你心肠?相看处痛都忘。休悲念精神无恙,暑云凉雨空园里,珍惜自身为上。”语极平白如话,老妪能解,而又情真意切。李渔论戏剧语言时提出:“贵浅不贵深。”又说:“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可见,仲氏是实践了李渔主张的。
然而,仲振奎毕竟不是曹雪芹。他二人身世虽然相似,但思想上差距很大。仲氏一生潦倒,却醉心于功名。他在悼亡诗中说:“一事语君难慰取,此身不上孝船。”对一生没有考上个举人,视为终身遗憾。这和借宝玉之口,批评热心于功名富贵为禄臺的曹雪芹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改编的《红楼梦传奇》竟引用了《后红楼梦》故事使宝、黛团圆。他在嘉庆四年刻本凡例中说:“前红楼梦读竟,令人悒怏于心,十日不快,仅以前书度曲,则歌筵将阑,四座无色,非酒以合欢义。故合后书为之,庶可拍案叫快,引觞发慌满也。”这种世俗之见,乃至连高鄂都不如了。除此之外,在前三十二折中,写一僧一道是骗子,史湘云成仙等等,均属败笔。当然,我们不必过多地苛求古人,仲氏毕竟是把《红楼梦》改编成戏曲的第一人,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