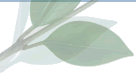|
(一)麝月的出场和神态
在前八十回中,麝月在怡红院的地位和表现并没有什么凸出的地方,很难紧随袭人和晴雯之后为四大丫鬟的第三名。然而从脂评出现后,我们知道麝月在后三十回是宝玉最后一段生命中的关键人物之一。脂评给我们见到的只是“云龙雾雨”,然而即使是一麟半爪已引起我们莫大的感慨,深信麝月和宝玉必有极扣人心弦的场面,足以补前八十回的不足而有余。
这一点应当说明在先,否则仅根据前八十回,读者有个印象,觉得麝月处处受袭人和晴雯的才貌所制压,一个是春花,一个是夏云,怡红院几乎是这二人的世界,而麝月的名字中固然有月字,绝非秋月,只能分到一点余润。这也是作者写作技巧圆浑周密的地方。大观园的场景宽阔,除了黛玉和宝钗之外,凤姐、湘云、探春等诸钗照样有施展的机会。怡红院的范围则有限制,而且诸丫鬟和宝玉的关系都是单纯的,她们的工作和行为也都依照同一规格,不可能为每个人另辟新天地,这样反而会破坏了整个格局。由此可见作者的节制和掌握的尺寸恰到好处。精彩的是作者把麝月写成一个具有自知和知人之明的性格,才不如袭人,貌不如晴雯,心甘情愿让二人处处占先,甘居下风,一点没有抑郁不忿之意。
在表面上,麝月的虚出场次数既少,而且只带上一笔,几乎可以说可有可无。第五回,宝玉在秦可卿房中床上午睡,众人伏侍他卧好,留下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丫鬟为伴。麝月居末,幸亏脂评捧场,给回麝月面子,如下:
袭人(一个再见。)(指第三回袭人安慰黛玉已出现过。)
媚人(二新出。)
晴雯(三新出。名妙而文。)
麝月(四新出。尤妙。)
可见她和晴雯同时第一次仅以名字虚出场。第九回,宝玉去上学读书,袭人一早起身替他收拾好书笔文物和衣服,伏侍他梳洗,然后谆谆劝告,宝玉一一应了,临行前又嘱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几句,后面还有个等字,可见不止她们两人,还有他人在内。第二次虚出也只是一笔带过。
要做宝玉的丫鬟,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媚人在第五回出现过一次之后,从此没有了下文;紫绡在第二十七回、二十八回和六十四回,出现过三次。在第二十八回,紫绡将元妃所赐之物送去黛玉处。程高本竟将紫绡之名完全删去,在第二十八回中以紫鹃代替紫绡,并将语气和称呼改过。英译者霍克思主要根据程高本,但看出此中不妥,宝玉送黛玉东西不派遣自己的丫鬟,却巴巴的将黛玉的紫鹃唤来,有悖常理,遂改为秋纹;这样一来宝玉名下的丫鬟,丢失了媚人(和袭人一对)、紫绡(和碧痕一对?)两名。从脂评中我们知道另外还有一位良儿(和坠儿一对),但从未在正文中出现过。和麝月成对的是檀云,她的名字于第二十四回、三十四回和五十二回出现过,根本没有动作和对白,可以说是连紫绡都不如的龙套,但她毕竟给保存下来了,一见第二十三回宝玉四时即事诗的“夏夜即事”的颔联:
窗明麝月开宫镜, 室霭檀云品御香。
二见第七十八回祭晴雯的“芙蓉诔”:
镜分鸾别,愁开麝月之奁;
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
与其说檀云在前八十回中有什么表现,不如说她占了和麝月成对的光,竟得留存下来。“梳飞”“折齿”可能是怡红细事之一,大概作者认为是衍文,在原作中删掉了,不必妄测。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利用檀云来衬托和巩固麝月的地位。
麝月的出场和她的为人一样,以低调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见第二十回,应该全录:
……宝玉惦着袭人,便回至房中,……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笑问道:“你怎么不同他们顽去?”麝月道:“没有钱。”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么些,还不够你输的。”麝月道:“都顽去了,这屋子交给谁呢。那一个又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妈妈子们,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该叫他们歇歇;小丫头子们也伏侍了一天,这会子还不叫他们顽顽去。所以让他们都去罢,我在这里看着。”宝玉听了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因笑道:“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罢。”麝月道:“你既在这里,越发不用去了。咱们两个说话顽笑岂不好。”宝玉笑道:“咱两个作什么呢?怪没意思的。也罢了,早上你说头痒,这会子没什么事,我替你篦头罢。”麝月听见,便道:“就是这样。”说着,将文具镜匣搬来,卸去钗钏,打开头发,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见了他两个,便冷笑道:“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宝玉笑道:“你来,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那么大福。”说着,拿了钱,便摔帘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宝玉便向镜内笑道:“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说,忙也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忽听唿一声帘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得说说。”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罢,又来问人了。”晴雯笑道:“你又护着,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话。”说着,一径出去了。这里宝玉通了头,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惊动袭人。
我们先将脂评对这一长段的批语录下,然后再分析讨论:
满屋里上头是灯,地下是火。
(脂批)灯节。
公然又是一个袭人。
(脂批)岂敢。
因笑道:“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罢……”
(脂批)每于如此等处,石兄何尝轻轻放过不介意来。亦作者欲瞒看官,又被批书人看出,呵呵。
咱们两个说话顽笑岂不好。
(脂批)全是袭人口气,所以后来代任。
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
(脂批)金闺细事如此写。
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
(脂批)虽谑话,亦少露怡红细事。
二人在镜内相视。
(脂批)此系石兄得意处。
忙向镜中摆手。
(脂批)好看煞,有趣。
晴雯又跑进来问道。
(脂批)麝月摇手为此,
可儿可儿。
(脂批)娇憨满纸,令人叫绝。
“我怎么磨牙了?”
(脂批)好看煞。
“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都知道。”
(脂批)找上文。
这一长段开头是麝月摆脱不开袭人的影响,连脂批都连说两次;结尾是麝月和晴雯两人之间的斗智和拌嘴,犹如两位名演员在舞台上演对手戏,精彩万分,脂批等于观众拍手和喝彩,但如果没有晴雯杀出,这一段如何结束煞费思量,可能成为反高潮。只有中段宝玉为麝月梳篦才是麝月的出场主戏,而且细想起来也非她不可,不可能是袭人,因为袭人要顾全自己的身分,岂可破坏规矩?也不可能是晴雯,麝月不在乎,因为知道轮不到自己,而晴雯必不能忍受他人讥笑她:“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麝月心里没有这种负担,故能坦然接受,而这一段真是金闺细事,由此可以看出麝月具有幽默感和另有一功的俏丽,不愧为四大丫鬟季军。
从宝玉眼中看来,麝月的神情和口吻“公然又是一个袭人”,脂砚也有同感。根据第四十六回鸳鸯向平儿发牢骚时所透露,麝月是元老派十来个人(晴雯之名漏提)之一,“从小儿什么话儿不说,什么事儿不作。”袭人和晴雯原在贾母房中,是贾母特地拨去服侍宝玉的。麝月居二人之下,其他众人之上,做宝玉的贴身丫鬟,一定经过考验和过滤认为合式方能中选。即使如此,她还是时常追随袭人学习为人和“干活”之道。第七十七回,晴雯被逐出园外,宝玉伤心万分,袭人劝解,宝玉先问:“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袭人回答得很勉强,宝玉进一步质问:“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还有孟浪该罚之处!”不要以为宝玉是个茶来伸手、饭来就口的大少爷,他的观人于微的能力极高,只是在裙钗前不轻露相而已
。
第七十四回,王夫人决定去检查怡红院,对凤姐和王善保家的说:“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可见她已有了主见。但说袭人麝月“笨笨的”是指二人见面时循规蹈矩,穿戴得素净大方,合乎身分,不像晴雯装扮得那样“花红柳绿”,并不是说她们姿色平庸和能力低下。宝玉房中连原名蕙香,后为宝玉改名为四儿的小丫鬟,都有“几分水秀”,只不过说过一句:“同日生日就是夫妻”的玩话就此被撵。袭人麝月可能算不上绝色,但至少是第一流人物,前论袭人时贾芸眼中的袭人可资证明。如果二人姿色毫不起眼,必不会见容于唯美派大师主持的怡红院。
麝月绝不止是袭人的模子里所刻出来的,一定有她可取的地方。论姿色,当然还不能和晴雯相提并论,但不会比袭人差哪里去,至少各有千秋,否则宝玉不会由她追随一生一世。最重要的一点是她能甘心居袭人晴雯之后,就像篮球队中最佳的守卫,在进攻时能及时供应晴雯和袭人投球入篮取分。晴雯是神射手,不幸在上半场就犯规离场,袭人是队长,在下半场也因伤离场,麝月独自支撑大局,其斗志和韧力犹在袭人之上,在最艰难的时刻才显露出她的美质----忠贞不移。我们唯有叹没有眼福,见不到后三十回麝月的具体表现,而前八十回有关她的描写实在和她的重要性不成比例,真是“人间的美中不足”。
(二)麝月的小传和遭遇
在前八十回,我们可以看到四大丫鬟的出场,但只能见到袭人的“传”和晴雯的“正传”,这两名词都见脂评。而根据脂评,我们知道宝玉和麝月同宝玉和小红单对单的主场戏或二人的传都见现已佚失的后三十回。至少我们可以根据脂评,为宝玉和她们的关系建立起一个大致不错的轮廓。未能窥到原稿自是莫大的憾事,但即使像电影说明书式的大纲也足以令人起无穷的感慨。
这并不是说麝月和小红在八十回里出了场之后就此失去影踪,因为她们在曹雪芹的有计划的经营手法下为后三十回提供了根据。“千里伏线”是作者的拿手技巧,同时还有侧笔和隐笔补足她们的性格,并为她们将来的作用安排好线索。
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夜宴,大家行酒令,抓花名签,湘云行完令后,绰起骰子来一掷个九点,数去该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这面上一枝荼蘼花,题着“韶华胜极”四字。那边写着一句旧诗,道是:开到荼蘼花事了。注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麝月问:“怎么讲?”宝玉愁眉忙将签藏了,说:“咱们且喝酒。”说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
宝玉生日宴而行花名签酒令,其间有深意存焉。《红楼梦》以花拟人,业经红学家指出,拙作《冷月葬花魂》一文亦曾提及,而贾宝玉为诸艳之冠,现聚诸艳于宝玉寿诞宴上,由各人掣花名签,花名之外,复有四字题句,反面更引旧诗一句,以暗喻身分和将来命运的预兆,这是《红楼梦》一向优为之的特有象徵手法。麝月掣到的一根是荼蘼花,花下的题字是:
韶华胜极
韶华意同韶光,指春光,青春不努力,亦有虚度韶光之说。荼蘼于春末诸花之后始开,与人无争。但“胜极”在字面上虽好,含意却非常不吉,因为中国人常用盛极而衰的说法,本书第十三回秦可卿向凤姐托梦,即嘱咐她“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盛极”其实就是衰败的开始,如果拿来和诗句并读则更为明显。无怪宝玉虽不能预知未来,而且更想不到会应在自己头上,但至少有好景不再的预感,所以“愁眉”将签藏了起来。签反面的一句诗:“开到荼蘼花事了”,根据蔡义江的考证,出自王琪的《春暮游小园》诗:
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
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梅于冬末春初即露绽(李纨掣到的是“老梅”),“海棠”于仲春盛开(海棠为湘云所掣到),荼蘼是春末最晚开的花,故云:“花事了”,同时注上又说在席诸人都各饮三杯“送春”,其为不吉之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所以宝玉将其藏去,并不加解释酒令,请大家各饮三口酒以应令,并命麝月再掷下去。麝月当然全不知情,宝玉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想到一切会应在他们两人身上。据蔡义江说,天棘是一种蔓生植物,其名出佛典,暗示宝玉的出处。
根据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先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其余则留待和脂评拼成比较更完整的构图。袭人和宝玉初试云雨情,拔了春花的头筹。晴雯和宝玉虽然始终只有虚名,但二人互爱极深,可以代表春花盛开怒放的气象。唯有麝月一开始即追随宝玉,自绛芸轩到怡红院,到贾家衰败和抄没,最后代替袭人服侍宝玉和宝钗夫妇二人,还遭受宝玉的“世人莫忍为”的“情极之毒”。真正对宝玉有始有终的并不是花袭人而是麝月。她是荼蘼花,眼巴巴看别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终于轮到自己开花时,春天已过,花事已了,命运对她无情到极点。
八十回以后,我们知道:
(一)贾家家道衰败,第七十二回,贾琏向鸳鸯央求偷运贾母的金银家伙暂押数千两银子以应家中急需,已可见端倪,以后当然每况愈下。
(二)贾家被抄没,原因已见上文,第二十回脂评在小红回答凤姐后有一条批,批小红为奸邪婢,岂能为怡红所容,故即逐之。在这条批后,接下去另有一条批加以纠正:“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可见“抄没”是促使贾家解体的大事。在抄没时,凤姐和宝玉曾有一个时期暂时在“狱神庙”受软禁,大概等于今天的隔离审查。袭人麝月等以及其他婢仆另有居处和安排。
(三)抄检很彻底,宝玉本身根本没有犯什么事,可能不久就恢复自由。可是他房中的大丫鬟袭人箱中却抄出了那条京城尽人皆知的茜香罗红汗巾,而这事必然会通知物主北静王。
(四)北静王一向很赏识宝玉,早已知道蒋玉菡同宝玉交换了汗巾,没有想到会在袭人箱中出现,认为这是天作之合。他很有可能协助为宝玉解除罪名,于是作主撮合袭人和蒋玉菡的良缘。
(五)宝玉自狱神庙出来后,首先便是要遣散怡红院各丫鬟,对袭人正不知如何是好。北静王这一措施刚好解决了他的难题,因为他也体会到这完全是天意,北静王之命难以拒绝,何况他心目中袭人和蒋玉菡正是理想的一对。
(六)以袭人和宝玉的关系,也决不会兴高采烈的和蒋玉菡享画眉举案之乐,置宝玉于不顾。她的安排见第二十回的脂评一条长批:
闲上一段儿女口舌,却写麝月一人。有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可见袭人虽去实未去也。这并不是说袭人找到了归宿才觅替身,而是出自真心为宝钗、宝玉、麝月三方面着想。其中关键固然是宝玉对麝月有好感,也要麝月感觉到得偿素愿才行得通。
(七)麝月服侍宝玉,宝钗夫妇二人,一定经过一段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潦倒和困苦时期。第十九回,宝玉去袭人家,炕上特为他摆了一桌子果品,“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底下有一条脂批:
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后部数十回“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这十字似是回目的上下联,上指食,下指衣,宝玉不见得独自一人挨这种苦日子,恐怕宝钗和麝月都是一同受难的伴侣,袭人怎么会和他们失去联络而不加援助,原作必有交代,我们目前只有一片空白。
(八)第二十回,李嬷嬷向凤姐发牢骚一段后有一条脂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叹叹!“花袭人有始有终”,讲得再清楚也没有,是回目名,可惜比其余的回目少了一字,脂评漏抄,但其真实性无可怀疑。所谓“始”大家都极清楚,所谓“终”绝不止敦促宝玉留用麝月,眼看他们生计为难,而是另有具体的安排。第二十八回,脂评回前总批第一条是:“茜香罗”、“红麝串”写于一回,(均见回目),盖琪官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者,非泛泛之文也。茜香罗原属琪官,红麝串是元春所赐,宝钗左腕笼着一串,宝玉要她褪下来瞧瞧,这又是千里伏线:茜香罗的主人在一百回后终于供奉红麝串的主人。蒋玉菡在第三十三回时已经在紫檀堡置有田地和房舍,此时必很富裕,承宝玉看得起以知己相待,又何况他是爱妻的旧东家,供奉他们夫妇自属天经地义。
(九)依照世人的标准,宝玉在家庭方面有了宝钗为妻和麝月为婢,其乐融融,物质生活方面,有蒋玉菡夫妇供奉,衣食无忧。以宝玉的能力,找份小差事不成问题,还可闲来作书画赚点外快。无奈宝玉绝不会以世俗人的眼光来看人生,和世俗人的生活方式来度余生。第二十一回,宝玉不听袭人劝解,不理他们,怡然自悦,闭户读南华经,在读经前有一长段批语:……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第三大病也。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撤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照猜想,宝玉之终于出家应在全书最末一回,“悬崖撤手”是上半回回目中的四字,下半回则是宝玉彻悟后见到“情榜”。(见第十八回屡次引的脂评:“至末回警幻情榜。”)“情榜”呼应第五回宝玉梦中见警幻仙并从她那里见到“正册”全文,副册和“又副册”的一小部份。末回则见到全部五册的“芳讳”,并知道自己原来是诸艳之冠,而且有极贴切的评语:“情不情”。他对诸钗个个有“情”,最后却做出最“不情”之举。换句话说,情到极点,反而变成“不情”。
(十)宝玉之所以出家,绝不会是为了生活上的困难。清人笔记说见到原作云宝玉流为乞丐或沦为柝更,毫无根据,要他受苦难,不必如此穷凶极恶。他出家更不是为了蒋玉菡和袭人的供奉有损他的自尊。真正的出家一定是由于大彻大悟,宝玉已先后在第二十一回续南华经,第二十二回听曲文,第三十六回悟到:“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到了第七十八回,看到园中之人四散,只剩下黛玉和袭人“可以厮混,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已一步步走近悟的边缘。等到“抄没”、“狱神庙”之后已是再世为人,只等待外界给他刺激,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人生是这么一回事。第二十六回,宝玉到潇湘馆去探视黛玉,“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下有一条容易为人所忽略的脂批:
与后文“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一对,可伤可叹。不妨推测宝玉在出家前到大观园去凭吊,主要对象之一当然是潇湘馆,从前神魂颠倒的地方竟然如此荒凉。整个大观园更是一片“断井颓垣”,连以前的“良辰美景”和“赏心乐事”都联想不起来,因为面目和人事俱非。黛玉早已病死,袭人也已出嫁,可见得各人眼泪的想法也未免天真失实。我曾在《论大观园》一文中说过:大观园是“人间仙境,因为是清净女孩子的堡垒,在其中过无忧无虑的生活,除了宝玉之外,其他男子一概不得入内。”脂评也说:“何等严肃清幽之地”。但这样一个人为的架构究竟无法持久,根本经不起岁月的侵蚀。大观园终于幻灭,也就是余英时所说,清净的“理想世界”终于回到肮脏的“现实世界”去。宝玉一向以侍候女孩子为已任,尽力保卫她们,不惜牺牲使她们获得暂短的欢乐,现在人和地,二者俱亡,连“周全园中红粉”的小愿望都落了空,生活的目的已不复存在,遂决定不再欺骗自己,只有撤手放弃尘世中的一切。
宝玉的“悬崖撤手”并不是一时的行动而是必然的发展结果,前八十回的伏线加上后来的遭遇,一定可以给我们圆满的解释,但这究竟是他单方面的决定,宝钗和麝月全不知情。猜想起来,作者也只写到宝玉方面的想法和做法为止,避开正面写宝钗和麝月的反应。这并不能减轻读者对宝钗和麝月的同情,宝钗守活寡,可是麝月却连名义也没有。花事竟如此了结,读者不禁再三为荼蘼花的遭遇扼腕。
(三)麝月的性格和谈吐
前文已说过,麝月自知才不如袭人,貌不及晴雯,如有她们在场,心甘情愿退居副手,丝毫没有委曲之感。没有了她,怡红院的日常工作难以顺利运行,袭人和晴雯之间必有摩擦,宝玉势必左右为难,何况她还带来了情趣。她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极易为人所忽视的角色。
她充袭人的下手,已到心领神会,合作无间的地步。第二十一回是一个神情跃然纸上的好例子:
……那袭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宝玉无了主意,因见麝月进来(脂批:“偏麝月来,好文章。”),便问道:“你姐姐怎么了?”(脂批:“如见如闻。”)麝月道:“我知道么!问你自己便明白了。”(脂批:“又好麝月。”)宝玉听说,呆了一回,自觉无趣,便起身咳道:“不理我罢,我也睡去。”说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脂批:“真乎?诈乎?”)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替他刚压上,只听忽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脂批:“文是好文,唐突我袭卿,我不忍也。”)也仍合目装睡。二人因此吵起嘴来,正闹之间,贾母遣人来叫宝玉吃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一并连麝月也不理,揭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不敢惊动你们。”麝月只得笑着出来,唤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日,(脂批:“斗凑得巧。”)因要茶,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儿的生得十分水秀。(脂批:“二字奇绝,多少姣态包括一尽。今古野史中,无有此文也。”)宝玉便问:“你叫甚么名字?”那丫头便说:“叫蕙香。”(脂批:“也好。”)宝玉便问:“是谁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脂批:“原俗。”),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脂批:“好极,趣极。”)又问:“你姊妹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第几?”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胜。”(脂批:“花袭人三字在内,说的有趣。”)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抿嘴而笑。(脂批:“一丝不苟,好精神。”)由这一段,可以看出麝月和袭人中间似乎有默契,根本无须喁喁细商,自能像一对网球双打冠军,合作得天衣无缝。无怪下文宝玉在写续南华经时,第一句便是: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
至于晴雯,麝月也是甘居其后,晴雯深知她的为人,二人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冲突。第三十一回,晴雯撕了宝玉的扇子后,宝玉又将麝月的扇子夺过来给晴雯撕。麝月虽不以为然,不肯助纣为虐,但也没有公然站在敌对立场。(这一段有动作和对白,写得“极精神”。)第五十一回,袭人因母病回家,凤姐派人来问,知是晴雯、麝月二人侍候,随亦放心。第六十二回,宝玉生日向长一辈的行礼,跟随他的是晴雯、麝月二人。第五十一回,宝玉喝茶叫袭人,侍候宝玉的麝月没醒,晴雯反而醒了,二人起来,麝月到外面去看月亮,晴雯衣服也不披,想偷偷去吓她,宝玉高声警告,二人互开玩笑,极为友好融洽。麝月笑她:“你就这么跑解马似的,打扮得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譬喻具体而别致,富于色彩和动作感,把晴雯写活了。第五十二回,晴雯抱病补雀金裘,宝玉这位少爷在旁越帮越忙,倒是麝月帮着拈线,一直陪她到钟鸣四下,补完为止。没有丝毫不甘愿做下手之意。
到了偶而有机会和秋纹在一起时,麝月总是居先,一来是当之无愧,二来是当仁不让。第五十四回,宝玉在贾母花厅上看戏,离席外走,随身跟随的是麝月、秋纹和小丫头。第六十七回,袭人出去探望凤姐,宝玉见了黛玉回来,见袭人不在,只有麝月秋纹在房中,因问:“你袭人姐姐那里去了?”麝月道:“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那里就丢了他。一时不见,就这样找。”说话很自然而有担待,并不是在逞强出头。
照说,麝月口气如此老练,应该是极好的事务人才,讵知大谬不然。第五十一回,晴雯生病请胡庸医来诊治,要给他一两银子作为诊费。宝玉和麝月跑到平时袭人常取钱的螺甸柜子去找:
……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簸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一把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我有趣。你倒成了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器似的。”那婆子站在外头台矶上,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个,再拣一块小些的罢。”麝月早掩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罢。这一段看了之后令人笑得肚痛。宝玉和麝月真是一对宝贝,明明是自己无知,一个反说:“这又不是做买卖”,另一个像唱双簧似的接下去说:“别叫那穷小子笑话。”细想麝月是元老派丫鬟,自小在贾府长大,书中没有提她有何家属,过的完全是供给制生活,完全不知外边的世面。生活在深宅大院中,一直没有机会同外界接触,无怪要和现实脱节,而婆子们要笑她们为副小姐了。脂评在回末总评仅提此节写得有无数波折,心细如发,大概是早已见到这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怡红院中,宝玉的主要精力放在周旋于袭人和晴雯之间,没有时间顾及他人,何况麝月处处故意退居二人之后?宝玉见了小红一面之后,翌晨不敢点名叫她,怕袭人等多心。唯有对芳官,宝玉公然亲近,因为芳官年纪还轻,大家以小妹妹视之,虽然后来照样也给王夫人所撵走。第七十三回,晚间赵姨娘的丫鬟小鹊来敲门密报,小心明天贾政问话,宝玉连忙准备理书,连累一房丫鬟们皆不能睡。
……读了没有几句,麝月又斟了一杯茶来润舌。宝玉接茶吃着,因见麝月只穿着短袄,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静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麝月笑指着书道:“你暂且把我们忘了,心且略对着他些罢。”麝月劝得很正经,但听见宝玉关切的话一定有说不出的“窝心”之感。在如此紧要关头,宝玉于两大之外,还留意到麝月衣衫的单薄,就凭这句话,麝月情愿侍候宝玉一辈子。
麝月的真正能耐当然在能言善道,而且似乎不用思索,每一字每一句都好像经过锤炼似的,既合情,又合理。正十二钗中的探春和麝月有相通之处,说起话来,立场坚定,一句紧一句,到最后占尽上风,使对方无词以对。中国人常说:“善于泳者溺于水。她们两个的长处就是从不滥用她们的口才,找到了适当的时间、事件和对象,她们方才发挥所长,打赢了漂亮的一仗,同时也大快人心。第五十九回,麝月对付春燕的母亲,发现她无理可喻,就另施妙计,所以没有显出真本事。第五十八回,芳官干妈欺侮她不算,还打她,惊动了宝玉、袭人和晴雯,这婆子居然死不认错,还在发蛮,袭人唤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几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
“你且别嚷。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骂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得骂得。谁许你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闲事了?都这样管,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越老越没了规矩。你见前儿坠儿妈来吵,你也来跟他学。你们放心。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老太太又不得闲心,所以我没回。等两日咱们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风煞一煞儿才好。宝玉才好了些,连我们不敢大声说话,你反打的人狼号鬼叫的。上头能出了几日门,你们就无法无天的,眼睛里没了我们。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他不要你这干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袭人找麝月真是知人善用,晴雯虽然聪敏绝顶,但失之性子过急,没有张弓就射,往往不能中的。看麝月这一番话理路清楚,一步紧一步,而且话中含有杀着,不由对方不认输。她真正的代表作见第五十二回,晴雯发现坠儿偷镯子,病中将她打发走了,结果她母亲来领她回家,先向晴雯求情。
晴雯道:“你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干。”那媳妇冷笑道:“我有胆子问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他纵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说话,虽是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们就使得,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晴雯听说,一发急红了脸,说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撒野,也撵出我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礼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便是叫名字,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是好养活。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何况我们。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老太太还说他呢。此是一件。二则我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话去,可不叫着名字回话,难道也称爷,那一日不把‘宝玉’两个字念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过一日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子,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的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晴雯其实没有称呼错,只是争辩时发急,说话乱了章法。麝月出面说话,倒也不是完全为了代晴雯解围,而是澄清原则。第一步讲大丫头们的身分,第二步讲直呼宝玉之名是贾母定下的规矩,第三步则讲每日回话时总是用宝玉之名而不尊他为爷,第四步是足下一向在三门外头混,不知里面的规矩,第五步是坠儿有什么话要说,可找林之孝家的来找二爷(此地不称宝玉,盖对林之孝家的而言)说话。最后是足下请便,此地非留步之所。这一段说来抑扬顿挫,胜过最雄辩的律师的陈词。如果麝月事先知道宝玉会出家,一定有极动人的解劝可听,可悲的是宝玉非常理可喻,而且“悬崖撤手”是那么决绝,又是不别而行,识大体的宝钗,能言善道的麝月根本没有机会施展所长。在麝月而言,她无法了解宝玉的动机,我本有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令人为她叹息。脂砚斋见到这一点,其中有一条批语可以用来为本节作结:“麝月闲闲无语,令余酸鼻,真所谓对景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