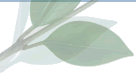|
鲁迅先生有一篇名为《“绛洞花主”小引》的杂文,其中文句经常被研究《红楼梦》的人所引用,是一篇颇具学术影响的文章。最近,邓遂夫先生与蔡义江先生围绕着贾宝玉的别号究竟应该是“绛洞花王”还是“绛洞花主”这一学术问题作了讨论。(邓文《宝玉是“绛洞花主”还是“绛洞花王”》发表于2000年1月21日《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及2000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蔡文《贾宝玉还应该是“绛洞花主”》发表于2000年4月28日《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 邓文《“绛洞花主”确属后人妄改--兼答蔡义江先生》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那么,《红楼梦》中的原文到底是“绛洞花主”还是“绛洞花王”?《鲁迅全集》中的有关注释是否应该作相应的修改呢?这虽然是一字之差(一“点”之差),却涉及到红学和鲁学这两大显学,涉及到对曹雪芹的思想境界和鲁迅的学术素养的理解和评价,是一个不能忽略不计的大问题。下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曹雪芹原著真笔到底是“绛洞花王”还是“绛洞花主”,关系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版本考证的问题,另一个是思想意义的问题。从版本考证的角度观照,我的看法,“花王”应该是曹雪芹原笔,“花主”乃是抄胥或印书人臆笔妄改。这从清末有正书局石印本《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时改题《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中“主”字上面的那一点远而歪明系后笔所添看得至为明显。邓遂夫先生查验,戚宁本(南京图书馆藏抄本《石头记》)上是“王”而非“主”。戚宁本与有正本的底本当属兄弟本关系,由戚宁本可推知有正本的底本也应当是“王”而不是“主”。而舒序本(清乾隆舒元炜序本《红楼梦》)、列藏本(原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石头记》)都有许多保持了雪芹真笔的他例(具体论证从略),此二本俱作“花王”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而作“花主”的甲辰本(1953年在山西发现的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梦稿本(清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却有多处由脂批本系统向程高本系统过渡的痕迹,反可证明“花主”是后笔所改。作“花主”的还有一个己卯本(清怡亲王府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但己卯本与庚辰本(北京大学藏七十八回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关系密切,如果说庚辰本抄自己卯本,为什么要将底本的“花主”改作“花王”呢?可见己卯本上的“主”字也极有可能是“王”字臆改。蔡先生也说“以己卯本说”,“‘主’字上的一点有点像后添”。这都是耐人寻味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庚辰本确是抄自己卯本,抄写时所依据的己卯本原是“王”而不是“主”,“主”字的那一点是后来才被添上去的。至于王府本(清蒙古王府藏抄本《石头记》)的“花玉”,我觉得“王”“玉”误写的解释比“主”字一点错置为“玉”的说法似乎更合理一些,把上面的点移到下面,这种“笔误”似不容易发生。甲戌本(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原大兴刘铨福藏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批说混世魔王“占(与)绛洞花王为对看”,点明正文乃“绛洞花王”,也说得很明白。
再从“对看”是否就是“对子”这一角度考察。显然,不能把脂批中的“对看”、“一对”等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对子看”,当然有对仗的意思,因为整部《红楼梦》的创作,曹雪芹原就有“大对称”、“春秋两扇面”(周汝昌语)的构思。但具体到某一字句,更着重的显然是思想意义和文章章法上的关联,是广义的“对”而非狭义的“对子”。宽泛地说,“绛洞花王”与“混世魔王”也算对子,严格地说,“绛洞花主”与“混世魔王”也不能算工整的对子,“混世”与“绛洞”无论平仄声调还是词性组合都不“对”。综上而观,无论从技术性考证还是从文义性理解,“花王”比“花主”的版本根据要更为扎实有力。
我历来主张,版本的考证不能孤立进行,不能迷信从版本到版本的所谓“科学”考证,而必须与文章、文笔的合理性审度结合起来,与文心、文胆的艺术创造性结合起来,对《红楼梦》尤其如此。因为各脂批本都是传抄本,它们虽然接近曹雪芹的原稿,却又并非曹雪芹的手稿,其中存在许多复杂情况。更关键的,是需要特别注意曹雪芹是一个极具独创性的作家,他行文遣词造句时常有“陌生化”特点,喜欢打破常规,出人意表。从这一角度考察,“绛洞花王”是远胜于“绛洞花主”的,作者赋予贾宝玉这个别号是有深刻的艺术作意的。这就是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已经指出的,贾宝玉有“三王号”:绛洞花王、混世魔王和遮天大王。这“三王号”是一个整体,是曹雪芹写出贾宝玉这样一位“古今不肖无双”叛逆者的隐喻性设计。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标榜圣王、先王的思想权威性,尧、舜、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等被尊为上古圣王和先王,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则被称为“素王”,即精神上的王,类似于古希腊所谓“哲学王”。曹雪芹赋予贾宝玉“三王号”,正是要树立一个与圣王、先王、素王分庭抗礼的“王”,一个思想和精神的异端。蔡先生所谓绛洞花王有“妖气”的感觉其实还是从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的立场出发的,而与曹雪芹的叛逆心灵却相远了。说“绛洞花王”像出自《西游记》,这种批评的视角倒有点歪打正着,因为“遮天大王”就是从“齐天大圣”来的。应该说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确实与孙悟空有精神的血缘维系,他们都是“大闹天宫”的,只不过贾宝玉所闹的“天宫”更具有形而上意味罢了。“绛洞花主”则有明显的封建士大夫气息,程伟元、高鹗信从“花主”不足为怪,那本来更符合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王雪香自号“护花主人”其实也说明同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倒可反证曹雪芹绝不会用“绛洞花主”之俗笔。
从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社各位诗人的雅号来说,贾宝玉为绛洞花王,林黛玉为潇湘妃子,薛宝钗为蘅芜君,王与妃“异性相吸”,王与君“同性相斥”,其暗喻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的情怀指向也是显豁的。同时,宝玉有两个“湘妃”,一个是潇湘妃子林黛玉,一个是“湘江水逝楚云飞”的史湘云,绛洞花王正等同于“圣王”大舜,作者将“花王”与“圣王”合二为一,偷天换日,暗度陈仓,其文心作意至为高妙。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史湘云的象征物是海棠(红香),而贾宝玉则来自于“赤瑕宫”。这正是“绛(赤色)”字的“两歌二牍之妙”(语出戚蓼生《序》)和“千皴万染诸奇”(脂批),直接关系到贾宝玉与“玉、钗、云”的爱情婚姻三部曲。具体论证参见拙著《〈石头记〉探佚》(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十七回暗写贾宝玉生日,众女儿为“花神退位”而“饯行”,是的确有微妙隐喻的。周汝昌在其红学著作中有详尽的论证。第二回贾雨村说到“正邪两赋之人”时冷子兴有“成则王侯败则贼”的话,有的本子作“成则公侯败则贼”,是“王侯”还是“公侯”?这又是一个与“花王”还是“花主”相似的版本认同问题,同样密切关系到《红楼梦》的思想宗旨和审美取向。
现在可以回到鲁迅先生的《“绛洞花主”小引》一文。在鲁迅撰写此文的时候,红学的发展还没有深入到今天的地步。上面论说的情况和道理鲁迅是不可能了解的。鲁迅也不是《红楼梦》研究的专家,他只是以一个思想家和杂文家的身分,拿《红楼梦》借题发挥,谈论他对人生的某种感悟而已。鲁迅依据当时的流传文本写作“绛洞花主”,这并不影响鲁迅的伟大。当然更不能因为鲁迅这么写了,就以之作为判断版本正误的依据,这应该是常识之内的事情。这与鲁迅的艺术感觉、思想深浅、学术素养等都毫无关系,而纯粹是一个“时代局限”问题。就鲁迅的个人气质、思想向度等方面观照,鲁迅倒是和曹雪芹以及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息息相通的。那种思想的叛逆性、深刻性,气质的敏感性、悲剧性,艺术天才的原创性,对传统文化既能“入”又能“出”的全面素养,都是可以“对看”,并引发深长思的。这方面的论述,红学界和鲁学界都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了。
最近我编了两副不太工整的对子,正可以作为本文的“点睛”之笔,写下来以供一粲:
上古圣王中古先王百代素王榜理学仁德
绛洞花王混世魔王遮天大王标情教意淫
抛砖引玉国魂在尊佚貂斥狗尾
叛道启蒙火炬传赖曹子接迅翁
《鲁迅全集》中《“绛洞花主”小引》一文的有关注释应该作相应的修改。本文或者可以作为修订时的参考吧。
2000年6月4日
|